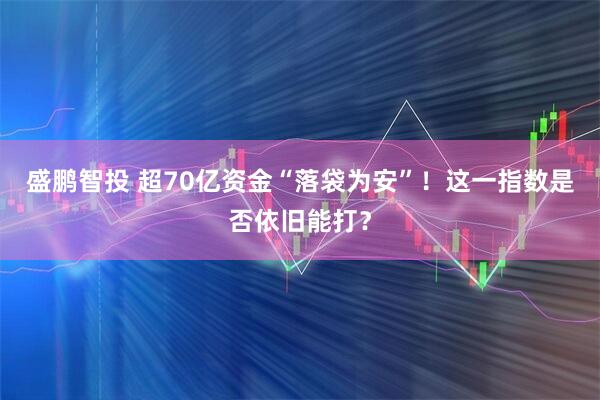1919年6月,陈独秀曾在自己创办的《每周评论》上发表过这样一段深刻的言辞:“世界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两个地方:一个是科学的研究室,另一个则是监狱。我们青年应当立志,在走出研究室后步入监狱,走出监狱后再回到研究室,这才是人生最高尚、最具价值的生活方式。只有这两个地方所孕育出来的文明天牛宝,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文明,才是值得追求的文明。”那时的中国,正面临着极大的政治动荡和深重的灾难。陈独秀作为当时的知名人物,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这些苦难,因此他发出了这样的呐喊。然而,令人意外的是,这些话语最终成了他个人命运的真实写照。
陈独秀的经历验证了他所说的“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,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”。他在1913年、1919年、1921年和1922年四度入狱,四次从监狱中获释,经历了他所言的这番起伏跌宕的生活。然而,到了1932年,当他第5次被捕时,这一次的情况却与以往完全不同,他再也没有像之前那样轻松地重新获得自由。
展开剩余77%1932年10月,尽管陈独秀早已不再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,早在1927年因右倾投降错误被停职,1929年正式被开除党籍,但他依然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。当时一些人认为国民党此举是想施压陈独秀,让他屈服于“党国”的要求,但陈独秀对于这些言论毫不理会。他只是将这次被捕当成了生活中的一件常事,毫不惊慌,甚至在被从上海押送到南京的列车上,竟然安然入睡,直到列车到站才被押解员粗暴地叫醒。
陈独秀从未将自己看作是一个囚犯,也没有因此而感到自卑。到了南京后,他首先要求当局为他添置衣物和棉被,理由是自己身体多病,捕捉时未带上任何御寒的衣物。作为一位知名人物,很多新闻记者请求进监狱采访他,而也有许多人因为仰慕陈独秀的书法,希望能得到他的“赐字”。而陈独秀并没有拒绝他们,许多青年军政人员在监狱中带着纸和笔求他题字天牛宝,陈独秀在那时挥毫写下了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等经典名句。他的书法不仅令这些青年军人们喜爱,也让他们感受到陈独秀身上那种刚强的气质,这与他作为囚徒的身份形成鲜明对比,完全没有低眉顺眼的模样,而是充满着一种力量与气节。
即便身在监狱,陈独秀依然受到了极高的尊敬,连看守的士兵对他也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态度。与此同时,监狱外的社会同样在为他呼吁和营救。1932年10月,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迅速传遍社会各界,掀起了前所未有的营救声浪。舆论的关注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程度,尤其是学术界。学术界的知名人物如蔡元培、杨杏佛、柳亚子、林语堂等纷纷在报纸上发声,呼吁蒋介石“矜怜耆旧,爱惜人才”,释放陈独秀,认为这对于中国的学术、文化事业是极为重要的。
国际上也有知名人物如杜威、罗素和爱因斯坦等,通过电报向蒋介石施压,要求释放陈独秀。这一事件引起了国际的广泛关注。面对这些压力,蒋介石的态度时而摇摆。最初,有人要求“清算陈独秀”,认为他曾是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,理应受到惩罚。但随着学术界和国际舆论的强烈呼声,蒋介石最终决定妥协,于11月24日发布了电文,决定将陈独秀的案件交由法院公开审理,而不是交给军事法庭,这为陈独秀带来了更多生存空间。
这次审理的过程中,陈独秀的态度依旧从容不迫。即便面对曾经的朋友和民国大律师章士钊的辩护,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,拒绝采纳章士钊的辩护意见。他以一篇数千字的《辩诉状》在法庭上阐述自己的立场,力辩自己是为国家未来和民族独立而奋斗,而不是“叛国”。尽管章士钊在庭上努力为陈独秀辩护,最终却因为用词不当而让陈独秀极为不满。陈独秀公开指出,章士钊的辩护并没有经过他的同意,认为他所用的辩护词曲解了自己的思想。这一番公开的较量让法庭上局面一度非常尴尬。
最终,法庭判定陈独秀犯“叛国罪”,判处有期徒刑13年,并褫夺公权15年。虽然他强烈抗议这一判决,表示自己并非叛国,而是坚定反对当时的政府,但判决依然没有改变。陈独秀的抗争不仅没有得到宽恕,反而将他送入了更长时间的监禁。直到1937年南京被日军轰炸,陈独秀才因减刑出狱,然而他的人生也因此走向了终点。
1942年5月27日,陈独秀病逝于四川江津的一处偏远村落,结束了他充满斗争和风雨的生命历程。这一生,他无论身处何种境地,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与信念,至死未曾改变。
发布于:天津市睿迎网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没有了
- 下一篇:千里马配资 黄百韬太傻还是太天真?固守碾庄,最后也没等到援军_徐州_国民党_兵团